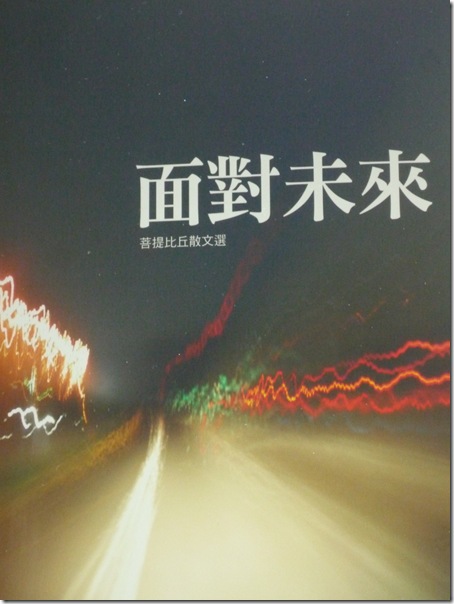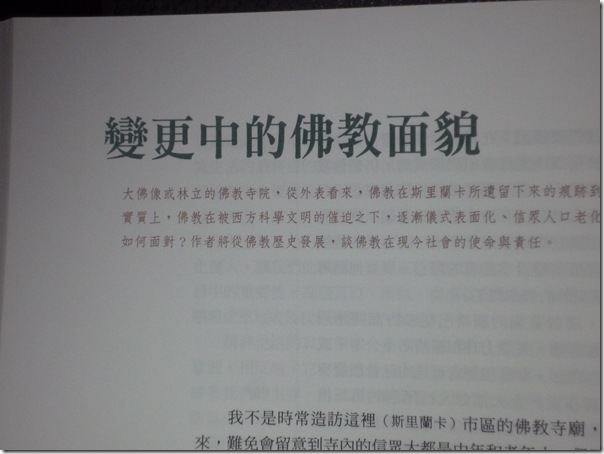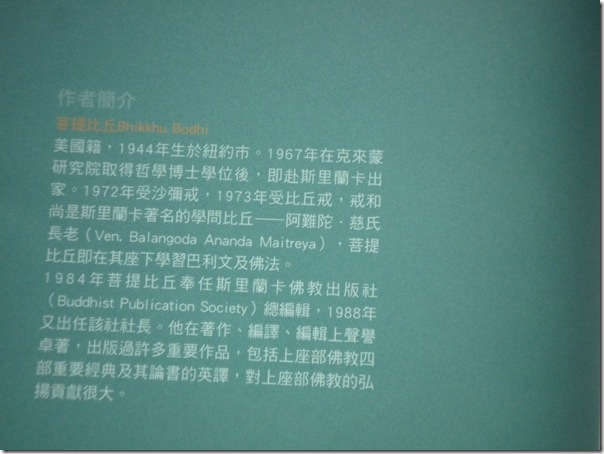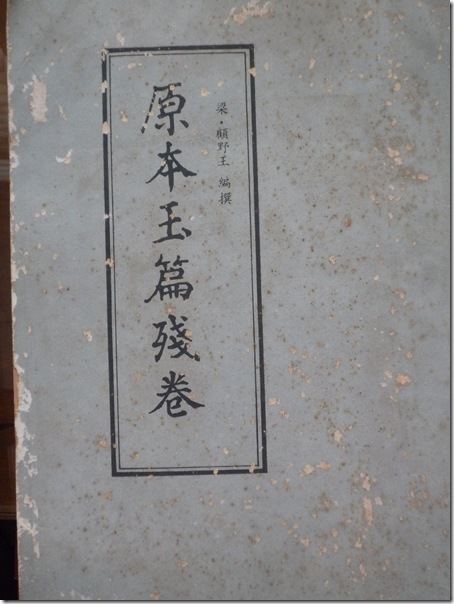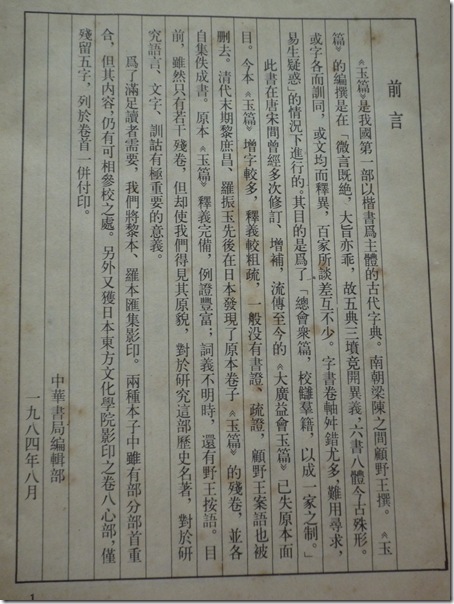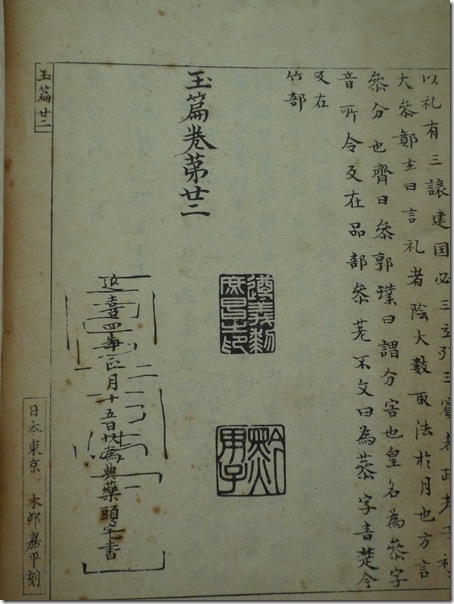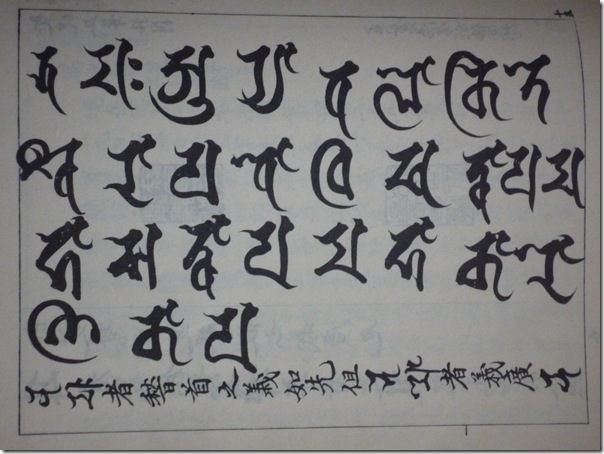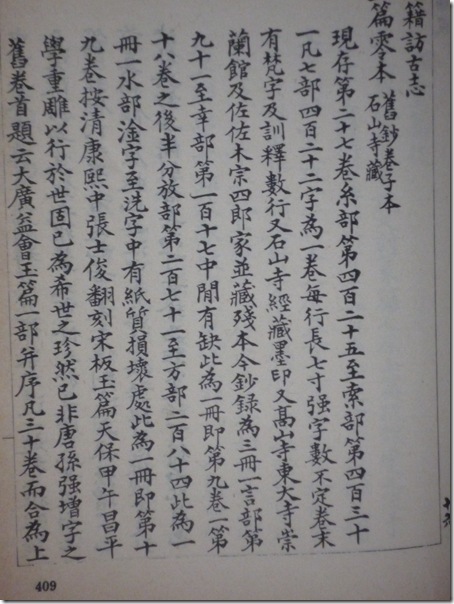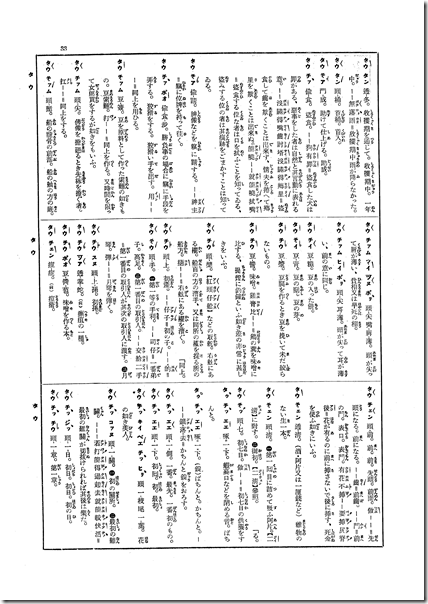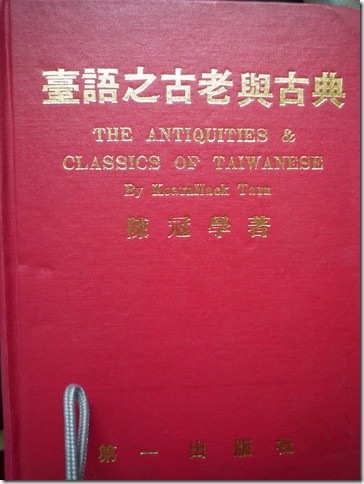以下引自部落格《藏經洞》
http://blog.sina.com.cn/s/blog_53c23f390100sk7y.html
方按:
下面是本人到2010年為止的論著目錄(不含翻譯、編譯、古籍整理),供有興趣者參考。凡本目錄未列而署有我名稱之論著,本人概不承認。
方廣錩論著目錄(1981~2010)
一、著作
01、《印度文化概論》,中國文化書院函授教材,1986年8月。
02、《印度》,上海辭書出版社,1988年9月。合作,統稿。
03、《佛教典籍百問》,今日中國出版社,1989年11月。台灣佛光出版社,1991年4月(繁體字版)。收入《佛教百問》(一),今日中國出版社,1997年9月。
04、《佛經中的民間故事》,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,1989年12月。合作,統稿。1995年12月選入中國青年出版社、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組織的《希望書庫》。1997年3月被花城出版社盜版,改名為《佛經民間故事》,陳鴻瀅編著。
05、《八~十世紀佛教大藏經史》,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,1991年3月。《八~十世紀佛教大藏經史》(法藏文庫本),台灣佛光出版社,2002年3月(第一次增訂本)。《中國寫本大藏經研究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6年12月(第二次增訂本)。
06、《中國所藏〈大谷收藏品〉概況——特别以敦煌遺書為中心——》,西域研究叢書之一,日本龍谷大學佛教文化研究所西域研究會,1991年3月。合作。
07、《中國古代宗教百講》,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,1993年12月。合作。
08、《道藏與佛藏》,新華出版社,1993年12月。合作。
09、《佛教典籍概論》,中國邏輯與語言函授大學教材,1993年7月。
10、《般若心經譯注集成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4年9月。
11、《敦煌佛教經錄輯校》(上、下),江蘇古籍出版社,1997年8月。
12、《中國文化通志˙佛教志》,上海人民出版社,1998年10月。
13、《敦煌學佛教學論叢》(上、下),中國佛教文化出版有限公司(香港),1998年8月。
14、《印度禪》,浙江人民出版社,1998年11月。
15、《中國佛教基礎知識》,宗教文化出版社,1999年1月。合作。
16、《敦煌壇經合校簡注》,山西古籍出版社,1999年9月。合作。
17、《英國圖書館藏敦煌遺書目錄(斯6981號——斯8400號)》,宗教文化出版社,2000年6月。
18、《那先比丘經試探》(法藏文庫本),台灣佛光出版社,2002年8月。
19、《道安評傳》,昆崙出版社,2004年7月。
20、《淵源與流變》,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,2004年5月。
21、《中國佛教》(五),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,2004年6月。合作。
22、《敦煌典籍與唐五代歷史文化》,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,2006年3月。合作。
23、《敦煌遺書散論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0年12月。
二、編著
01、《中國思想寶庫》,中國廣播电視出版社,1990年8月。合作主編。
02、《東方思想寶庫》,中國廣播电視出版社,1990年8月。合作主編。
03、《禪詩鑒賞詞典》,人民大學出版社,1993年2月。合作主編。
04、《印度宗教與中國佛教》,《南亞研究》增刊,1988年12月。合作主編。
05、《藏外佛教文獻》,第一輯~第九輯,宗教文化出版社, 1995年12月~2003年7月。第十輯~第十五輯,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,2008年7月~2010年7月。主編。
06、《中國佛教文化大觀》,北京大學出版社,2001年1月。主編。
07、《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》,江蘇古籍出版社,1~5册,1999年。6~7册,2001年。副主編。
08、《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》,第1册至第136册,北京圖書館出版社,2005年~2010年。常務副主編。
09、《中國宗教歷史文獻集成˙藏外佛經》,共30册,黄山書社,2006年,主編。
10、《中華大典˙哲學典˙佛道諸教分典》,雲南教育出版社,2007年10月。主編。
三、參與詞條撰寫
01、《中國大百科全書˙哲學卷》,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,1987年10月。
02、《中國大百科全書˙宗教卷》,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,1988年1月。
03、《文獻學詞典》,江西教育出版社,1991年1月。
04、《中外文化辭典》,南海出版公司,1991年11月。
05、《哲學大辭典》,上海辭書出版社,1992年10月。
06、《敦煌學大辭典》,上海辭書出版社,1998年12月。
07、《外國哲學大辭典》,上海辭書出版社,2000年7月。
08、《佛教大辭典》,江蘇古籍出版社,2002年12月。
四、論文
001、《有神論與宗教》,載《南亞與東南亞資料》,1981年第2期。
002、《漢譯〈那先比丘經〉譯本譯時考》,載《世界宗教研究》,1981年第3期。
003、《略談初期淨土大師及淨土宗的形成》,載《青海社會科學》,1981年第4期。
004、《中國佛教研究的新收獲》,載《讀書》,1982年第8期。
005、《月官身份考及其它》,載《南亞與東南亞資料》,1983年第1期。
006、《〈那先比丘經〉中的靈魂觀》,載《南亞研究》,1993年第1期。
007、《迦毗羅衛何處是》,載《法音》,1983年第6期。
008、《從歷史必然性中追踪中國佛學思潮的起伏》,載《中國社會科學》,1983年第4期。
009、《初期佛教的五陰與無我》,載《中國佛學論文集》,陕西人民出版社,1984年6月。
010、《元代官刻大藏經的發現》,載《文物》,1984年12期。合作。
011、《吠陀文獻》,載《世界宗教資料》,1984年第3期。
012、《釋迦“聖人”的故事》,載《世界歷史知識》,1984年第4期。收入《史海探迷》,世界知識出版社,1986年2月。
013、《龍樹及其著作與思想》,載《南亞研究》,1985年第2期。
014、《敦煌佛典經錄札記》,載《敦煌學輯刊》,1986年第1輯。
015、《元代官刻大藏經的考證》,載《世界宗教研究》,1986年第2期。合作。
016、《試論印度河文明衰落的原因》,載《南亞研究》,1986年第3期。
017、《佛教的起源與傳播》,載《世界歷史大事記》,重慶出版社,1986年9月。
018、《元史考證兩篇》,包括《元代徽政院詹事院置廢考》與《元代官刻大藏經中的兩份職名錄考釋》,載《文史》第29期,中華書局。
019、《敦煌寫經〈佛說孝順子修行成佛經〉簡析》,載《南亞研究》,1988年第2期。
020、《敦煌遺書中的佛教著作》,載《文史知識》,1988年第10期。
021、《佛教經錄雜談》,載《佛教與中國文化》,中華書局,1988年10月。
022、《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有益反思》,載《人民日報》,1988年10月7日。
023、《千字文帙號是智昇所創辨》,載《印度宗教與中國佛教》,《南亞研究》增刊,1988年12月。
024、《近兩年印度宗教哲學研究的回顧》,載《南亞研究》,1989年第1期。
025、《敦煌遺書〈沙洲乞經狀〉研究》,載《敦煌研究》,1989年第2期。收入《隋唐佛教會議論文集》,陝西三秦出版社,1990年。
026、《佛教的世界模式與諸神》,載《南亞與東南亞資料》,1989年第2期。
027、《悠久的歷史》,載《南亞與東南亞資料》,1989年第2期。
028、《因明不等於佛家邏輯》,載《因明新探》,甘肅人民出版社,1989年9月。
029、《從吠陀到奥義書》,載《南亞研究》,1989年第3期。
030、《也談敦煌寫本〈眾經別錄〉的發現》,載《中國敦煌吐鲁番學會研究通訊》,1990年第1期。
031、《吐蕃統治時期敦煌流行的偈頌帙號法》,載《敦煌學輯刊》,1990年第1期。
032、《漢文大藏經帙號探原》,載《世界宗教研究》,1990年第1期。
033、《敦煌佛教研究的回顧與展望》,載《中國文化》,1990年6月第2期。
034、《關於敦煌遺書〈佛說佛名經〉》,載《敦煌吐魯番學研究論文集》,漢語大詞典出版社,1990年6月。
035、《關於佛教起源的幾點思考》,載《南亞研究》,1990年第2期、第3期蓮載。
036、《敦煌遺書中的〈般若心經〉譯注》,載《法音》,1990年第7期。
037、《關於敦煌遺書之分類》,載《中國敦煌吐鲁番學會研究通訊》,1991年第1期。
038、《北京圖書館藏敦煌遺書勘查初記》,載《敦煌學輯刊》,1991年第2期。日譯:《禪文化研究所紀要》第23號,日本京都禪文化研究所,1997年6月。
039、《佛學名著叢刊出版說明˙弘明集˙廣弘明集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1年8月。
040、《佛學名著叢刊出版說明˙法苑珠林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1年8月。
041、《敦煌藏經洞封閉原因之我見》,載《中國社會科學》,1991年第5期。收入《北京圖書館同人文選》第二輯,書目文獻出版社,1992年9月。英譯:載《中國社會科學》(英文版),1994年第3期。
042、《吐魯番出土漢文佛典述略》,載《西域研究》,1992年第1期。
043、《禪,從印度到中國》,載《禪學研究》,1992年第1期。
044、《禪之史话》,載《佛教文化》,1992年第1期。
045、《俄藏大乘錄研究》,載《北京圖書館館刊》,1992年第1期。
046、《佛藏源流》,載《南亞研究》,1992年第3期。
047、《敦煌漢文遺書分類法(草案)附說明》,載香港《九洲學刊》,1992年敦煌學專刊。
048、《對黃編<六百號敦煌無名斷片的新標目>之補正》,載《中華文史論叢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2年12月。
049、《圓瑛法師的淨土思想》,載《圓瑛大師圓寂四十周年紀念文集》,古吳軒出版社,1993年9月。
050、《佛教的時間與空間》,載《南亞研究》,1993年第4期。
051、《禪藏與敦煌禪籍》,載《禪學研究》第2輯,江蘇古籍出版社,1994年。收入《禪與東方文化》,商務印書館國際有限公司出版,1996年2月。
052、《佛學名著叢刊出版說明˙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4年5月。
053、《<大般涅槃經>的卷數》,載《南亞研究》,1994年第3期。
054、《關於印度初期佛教研究的幾個問題》,載《南亞研究》,1994年第1期。
055、《敦煌遺書中的<金剛經>及其注疏》,載《世界宗教研究》,1994年第4期。又載《新疆文物》,1995年第1期。
056、《敦煌遺書中<維摩詰所說經>及其注疏》,載《敦煌研究》,1994年第4期。
057、《四川大足小佛灣大藏塔考》,載《佛學研究》第二辑,佛教文化研究所,1994年。
058、《浮屠經考》,載《國外漢學》第一輯,商務印書館,1995年1月。《<浮屠經>考》(修訂稿),載《法音》,1998年第6期。
059、《敦煌禪文獻與宗密禪藏》(日文),载日本《中外日报》,1995年2月14日第一版。
060、《敦煌之息吹》(日文),載日本《朝日新聞》(大阪)1995年6月10日。後收入日本《文物》雜誌。
061、《敦煌經帙》,載《敦煌學輯刊》,1995年第1輯。收入《敦煌吐魯番研究論集》,書目文獻出版社,1996年6月。
062、《斯坦因敦煌特藏所附數碼著錄考》,載《一九九○年國際敦煌學學術討論會論文集》,遼寧美術出版社,1995年7月。
063、《關於敦煌遺書北新八七六號》,載台灣《九洲學刊》,1995年第3期。
064、《關於禪藏與敦煌禪籍的若干問題》,載《藏外佛教文獻》第一輯,宗教文化出版社,1995年12月。收入《中國嵩山少林寺建寺1500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,宗教文化出版社,1996年6月。
065、《〈藏外佛教文獻〉出版前語》,載《法音》,1995年第12期。
066、《中國大藏經研究的回顧與展望》(日文),載龍谷大学《佛教文化研究所紀要》第34輯。
067、《敦煌遺書中的佛教文獻》,載《西域研究》1996年第1期。
068、《海外大藏經編輯及電子版大藏經的情況》,載《法音》,1996年5月。又收入《藏外佛教文獻》第二輯,宗教文化出版社,1996年8月。
069、《大藏經編纂及其光電化爭議》,載《藏外佛教文獻》第二輯,宗教文化出版社,1996年8月。
070、《〈藏〉外話佛教》,載《佛教文化》,1996年第4期、第5期蓮載。
071、《令人遺憾的書評》,載《佛學研究》第四輯,佛教文化研究所,1996年。
072、《簡論中國佛教的特點》,載《世界宗教文化》,1996年夏季號。
073、《<淨度三昧經>的目錄學考察》(中文、日文),載《七寺古逸經典研究叢書》第二卷,日本大東出版社,1996年4月。又以《從經錄著錄看〈淨度三昧經〉的真偽》為名,載《周紹良先生欣開九秩慶壽文集》,中華書局,1997年3月。
074、《同修大藏,再造輝煌》,載台灣《21世纪的宗教展望論文集》,關天師天心慈善基金會,1996年。
075、《〈大正新修大藏經〉評述》,載《聞思》,華文出版社,1997年3月。
076、《敦煌遺書中所存全國性佛教經錄研究》,载《古典目錄學研究》,天津古籍出版社,1997年3月。
077、《佛典電子化發展迅速》,載《人民政協報》,1997年4月10日第三版。
078、《論大藏經的三種功能形態》,載台灣《宗教哲学》,第3卷第2期,1997年4月。
079、《評敦煌願文集》,載《敦煌吐魯番研究》第二輯,北京大學出版社,1997年10月。
080、《談藏外佛教文獻的选選篇、錄校與其他》,載《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研究通訊》,1997年第1期。
081、《敦煌遺書中的〈妙法蓮華經〉及有關文獻》,載台灣《中華佛學學報》第十期,1997年7月。《敦煌遺書中的<法華經>及其注疏》(修訂稿),載《法源》,1998年月。
082、《〈藏外佛教文獻〉整理出版近況》,《古籍整理出版情況簡報》,1997年第十期。
083、《敦煌遺書中の<法華經>註疏》,載日本《中外日報》,1997年11月15日。中文本:《敦煌遺書中的<法華經>注疏》,載《世界宗教研究》,1998年第二期。
084、《敦煌遺書鑒别三題》,載《佛教與中國傳統文化》,宗教文化出版社,1997年12月。英譯:《Three puestions in the appraisal of Dunhuang manuscripts》,載3 Dunhuang Manuscript Forgeries,英國圖書館出版,2001年。
085、《隨缘做去,直道行之》,載《南海》雜誌,1998年第1期。
086、《西子湖畔苦行僧》,載《南海》雜誌,1998年第2期。
087、《初期佛教的思想》(上),載《東方文化集刊》2,商務印書館,1997年2月。
088、《也談青州龍興寺窖藏佛像殘破之謎》,載《佛教文化》,1998年第1期。
089、《我與佛教》,載《佛教文化》,1998年第2期。
091、《金陵刻經處與方册本藏經》,載《法音》,1998年第5期。
090、《大梵寺佛音──敦煌莫高窟壇經讀本評價》,載《敦煌研究》,1998年第1期。
092、《敦煌<壇經>新出殘片跋》,載日本《禪學研究》第76號,1998年3月。
093、《關於初傳期佛教的幾個問題》,載《法音》,1998年第8期。
094、《兩箱敦煌經卷殘片的再發現》,載《南海》雜誌,1998年9月。《光明日報》(删節稿),2009年8月5日。
095、《天台教典入藏考》,載《藏外佛教文獻》第五輯,宗教文化出版社,1998年9月。
096、《敦煌遺書錄校五人談》,載《俗語言研究》第五期,1998年月。合作。
097、《讀<瑜伽經>》,載《中國佛學》第一卷第一期,1998年10月。
098、《關於敦煌遺書的流散、回歸、保護與編目》,《中國社會科學院通訊》改版試刊12號、13號連載,1998年11月18日、27日。
099、《天津文物公司藏敦煌寫經》之“序”及“叙錄”,載《天津文物公司藏敦煌寫經》,文物出版社,1998年10月。
100、《浙江圖書館所藏敦煌遺書目錄》,載《敦煌研究》,1998年第4期。合作。
101、《南京圖書館所藏敦煌遺書目錄》,載《敦煌研究》,1998年第4期。合作。
102、《大藏經研究》,載《中国宗教研究年鑑(1996)》,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,1998年11月。
103、《浙江博物館所藏敦煌遺書目錄》,載《敦煌學輯刊》,1998年第1期。合作。
104、《中國散藏敦煌遺書目錄》(一),载《敦煌學輯刊》,1998年第2期。
105、《就敦煌本壇經致洪修平的信》,載《惠能評傳》,南京大學出版社,1998年12月。
106、《道安避難行狀考》,載《學術集林》卷十五,上海遠東出版社,1999年1月。
107、《關於佛教傳入兩千年的幾個問題》,載《正法眼》,1999年第1期。
108、《再有幾個地球便如何》,載《環境與東亞文明》,山西古籍出版社,1999年2月。日譯:載《東洋的環境思想之現代的意義》,日本農山漁村文化協會出版,1999年3月。收入《佛教文化與現代社會》,天津人民出版社,2002年10月。
109、《初期佛教的禪觀與念佛》,載《第二届兩岸禪學研討會論文集——念佛與禪禅》,台灣慈光禪學研究所、中華佛教禪淨協會出版,1999年10月。
110、《關於國家圖書館善本部所藏的日本天平藤原皇后施經》,載《法音》,1999年第11期。
111、《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前言》,載《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》,江蘇古籍出版社,1999年9月。又载《文献》,1999年第4期。
112、《敦煌藏經洞封閉年代之我見》,載《敦煌文藪》,台灣新文豐出版公司,1999年。
113、《哲人雖萎,風範長存——紀念入矢義高先生》,載《入矢義高先生追悼文集》,汲古書院,2000年3月。
114、《關於敦煌遺書的編目》,载《北京理工大學學報》(社會科學版),2000年第2期。
115、《寧夏西夏方塔出土漢文佛典叙錄》,載《藏外佛教文献》第七輯,宗教文化出版社,2000年6月。
116、《楊文會編藏思想》,載《中華佛學學報》第十三期,2000年月。
117、《宣宗關於歸義軍的詔勅》,載《敦煌研究》,2000年第3期。
118、《〈敦煌之戀〉也荒唐》,載《書品》,2000年第4期。
119、《呼籲編纂敦煌遺書總目》,載《古籍整理通讯》。
120、《初期佛教的年代、分期及其他》,載《佛教與歷史文化》,宗教文化出版社,2000年12月。
121、《日本對敦煌佛教文獻之研究》,載《中日近現代佛教的交流與比較研究》,宗教文化出版社,2000年6月。
122、《發掘を待つ最後の“寶藏”》,載日本《中外日報》,2001年1月30日第一版。中文本:《呼喚<羽田亨目錄>中的敦煌遺書早日面世》,載《中華讀書報》,2001年11月21日。
123、《關於江泌女子僧法誦出經》,載《普門學報》,2001年第2期。又載《藏外佛教文獻》第九輯,宗教文化出版社,2003年7月。
124、《關於敦煌本〈壇經〉》,載《敦煌文獻論集》,遼寧人民出版社,2001年5月。收入《四祖黃梅寺與中國》,湖北人民出版社,2006年6月。
125、《略談初期佛教的思想》,載《華林》第一卷,中華書局,2001年月。
126、《影印敦煌遺書〈大乘無量壽經〉序》,載《敦煌學輯刊》,2001年第1期。
127、《怎樣讀佛經》,載《世界宗教文化》,2001年第2期。
128、《二十一世紀中國佛教的走向》,載《法音》,2001年第9期。
129、《從「敦煌學」的詞源談起——兼為王冀青先生補白》,載《敦煌學輯刊》2001年第2期。
130、《僧祐的疑經觀》,載日本《中外日報》,2001年11月22日第一版。中文本:載《世界宗教研究》。
131、《為什麼想要編一本<中國佛教文化大觀>》,載《佛教文化》,2001年第4期~第5期。
132、《介紹清咸豐刻本〈武帝明聖經〉》,載《關羽、關公和關聖》,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,2002年1月。
133、《季羨林與佛教研究》,載《敦煌研究》2002年第1期,2002年2月。
134、《信息時代的佛教目錄學》,載台灣《佛教圖書館館訊》第29輯,2002年3月。
135、《對下個世紀佛教的幾點思考》,載《戒幢佛學》第一卷,岳麓書社,2002年4月。
136、《漫談禪宗研究》,載《文史知識》,2002年第四期。在本人不知情的情況下,該文被人修改發表。正確文本請看新浪博客:藏經洞/方廣錩。
137、《敦煌本壇經首章校釋疏議》,載《中國禪學》第一期,中華書局,2002年8月。
138、《〈晉魏隋唐殘墨〉綴目》,載《敦煌吐魯番研究》第六卷,北京大學出版社,2002年8月。
139、《「草創期的敦煌學」研討會散記》,載《敦煌吐魯番研究》第六卷,北京大學出版社,2002年8月。
140、《談粘葉裝》,載《國家圖書館學刊˙西夏研究專號》,2002年增刊。
141、《關於敦煌遺書的幾個問題》,載《人文視野》,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,2002年1月。
142、《禪與禪宗》,載《白雲論壇》第一卷,大連圖書館,2002年1月。
143、《藏經洞與敦煌遺書》,載《白雲論壇》第一卷,大連圖書館,2002年1月。
144、《中國佛教經論序跋記集序》,載《中國佛教經論序跋記集》,上海辭書出版社,2002年9月。
145、《曲肱齋全集》序,載《曲肱齋全集》,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,2002年9月。
146、《道安著作綜述》,載《法源》總二十期,2002年。
147、《收藏題跋から見た草創期の敦煌學》,载《草創期の敦煌學》,知泉書館,2002年12月。中文本:《初創期的敦煌學》,載《行願大千》,宗教文化出版社,2006年9月。
148、《從〈敦煌遺書總目索引新編〉前百號,談敦煌佛教文獻的著錄》,載《覺群學術論文集》,第二輯,商務印書館,2002年11月。
149、《金剛經贊研究》序,載《金剛經贊研究》,宗教文化出版社,2002年12月。
150、《關於敦煌本〈壇經〉的幾個問題》,載《田中良昭博士古稀紀念論集,禪學研究の諸相》,大東出版社,2003年2月。
151、《印度佛教講座》(一)~(五),載《佛教文化》,2003年第2期~第6期。
152、《曾坐春風點愚遲》,載《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教育通訊》,2003年第1期。
153、《談信雅達》,載《靈山海會》總第八期,2003年夏。
154、《敦煌寺院所藏大藏經概貌》,載《藏外佛教文獻》第八輯,宗教文化出版社,2003年7月。
155、《〈慧琳音義〉與唐代大藏經》,載《藏外佛教文獻》第八輯,宗教文化出版社,2003年7月。
156、《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佛教研究的回顧與展望》,載《中國社會科學院院報》,2003年8月14日。《新華文摘》轉載,2003年第11期。
157、《蒙古文甘珠爾丹珠爾目錄前言》,載《蒙古甘珠爾丹珠爾目錄》,蒙古人民出版社,2003年。
158、《為中國建設新文化鋪路墊石》,載《中華讀書報》,2003年。
159、《中國佛教哲學研究的里程碑》,載《普門學報》,第22期,2004年7月。
160、《偽梁武帝書法華經跋》,載《哲學、宗教與人文》,商務印書館,2004年12月
161、《關於佛教起源的幾點思考》,載《中國宗教研究四十年》,宗教文化出版社,2004年9月。
162、《中華大藏經續編的編纂》,載《光明日報》,2005年7月14日。
163、《繼絕存真,傳本揚學--中華再造善本工程訪談錄》,載《人民日報》,2005年10月10日。
164、《遼大字本的定名與存本》,載《中國學術》總第18辑,商務印書館,2005年1月。
165、《略談中華大藏經在漢文大藏經史上的地位》,載《書品》,2005年第3期。
166、《敦煌遺書斯5665號與經摺裝》,載《文史》,2005年第1輯。
167、《中國宗教文獻研究的新動向》,載《中國宗教》,2005年第11期。
168、《敦煌藏經洞封閉之謎》,載《敦煌與絲路文化學術講座》,北京圖書館出版社,2005年1月。據錄音整理,未經本人審定。
169、《勝樂輪經及其注疏解讀序》,載《勝樂輪經及其注疏解讀》,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,2005年。
170、《敦煌遺書編目所用數據庫及數據數據》,載《敦煌學知識庫學術論文集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6年。
171、《敦煌已入藏佛教文獻簡目》,載《敦煌研究》,2006年第1期。
172、《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北敦00337號小考》,載《文獻》第1期,2006年3月。
173、《摩利支天----金剛寺本與敦煌本》(日文),載日本《いくら》第1期,2006年3月。
174、《關於敦煌遺書的保管與修復》,載《文明的守望》,北京圖書館出版社,2006年5月。
175、《敦煌遺書與奈良平安寫經》,載《敦煌研究》,2006年第6期。
176、《略談敦煌遺書的二次加工及句讀》(韓文),載韓國《漢文讀法及東亞文字》,2006年12月。
177、《漢文大藏經の定義、時期區分およびその特徵》(日文),載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編《中國宗教文獻研究》,日本臨川書店,2007年2月。
178、《禪宗優秀文化與構建和諧社會學術研讨會綜述》,載《禪和之聲》,宗教文化出版社,2007年3月。摘要载《世界宗教研究》,2007年第1期。
179、《〈祖堂集〉中的「西來意」》(上),載《世界宗教研究》,2007年第1期。又載《禪和之聲》,宗教文化出版社,2007年3月。中国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《宗教》轉載,2007年第4期。
180、《寫本藏經的的特點與分期》,載《文史哲》,2007年第3期。
181、《試論佛教的發展中的文化匯流》,載《華東師大學報》,2007年第1期。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《宗教》轉載,2007年第3期。
182、《試論佛教的發展中的文化匯流附贅語》,載《法音》,2007年第3期。又載《普門學報》第43期,2008年1月。載日本東京《國際佛教學大學院大學研究紀要》第11號,平成19年(2007年)。
183、《讀方立天文集》,載《法音》,2007年第7期。
184、《讀周叔迦佛學論著全集》,載《書品》,2007年第2輯。
185、《敦煌遺書三題》,載《吳越佛教》第二卷,宗教文化出版社,2007年4月。
186、《關於佛說孝順子修行成佛經的新資料》,載《南亞研究》,2007年第2期。
187、《杭州靈隱寺宋代貝葉經之考察》,載《中華文史論叢》,2007年第1期(總85期)。英譯:Findings about a Northern Song Dynasty Pattra Sutra Kept the Lingyinsi Temple,Annual 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for Advanced Buddhology at Soka University,vol.11,March 2008。JAPAN TOKYO。
188、《要進一步重視對宗教古籍的保護》,光明日報,2007年9月8日第五版。
189、《敦煌本壇經錄校三題》,載《禪與人間佛教佛學研究論文集》,台灣佛光山文教基金會,2007年5月。又載《藏外佛教文獻》第十輯,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,2008年7月。
190、《玄奘五種不譯三題》,載《法音》,2006年第10期。又載《第三届玄奘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,四川辭書出版社,2008年1月。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《宗教》轉載,2007年第2期。
191、《中國書店藏敦煌文獻前言》,載《中國書店藏敦煌文獻》,中國書店,2007年8月。
192、《佛教大藏經研究論稿序》,載《佛教大藏經研究論稿》,宗教文化出版社,2007年8月。
193、《劉師禮文中禮拜法初探》,載《世界宗教研究》,2008年第1期。
194、《讀雲南阿咤力教典籍隨筆》,載《虛雲法師與雞足山佛教》,宗教文化出版社,2008年5月。
195、《英國圖書館藏敦煌遺書中新發現四件早期中國印刷品》,載《轉型期的敦煌學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7年11月。
196、《敦煌遺書與佛教研究——新材料與新問題》,載《佛學百年》,武漢大學出版社,2008年6月。
197、《漫談敦煌遺書》,載《學習與与探索》,2008年第3期。
198、《雲南阿咤力教經典研究序》,載《雲南阿咤力教經典研究》,中國書籍出版社,2008年3月。
199、《懷念柳田聖山先生》,載《柳田聖山先生追悼文集》,柳田聖山先生追悼文集刊行會,2008年11月。
200、《百年前的一樁公案》,載《敦煌研究》,2009年第1期。
201、《任繼愈先生是怎樣培養學生的》,載《社會科學論壇》,2009年10年。收入《我們心中的任繼愈》,中華書局,2010年4月。